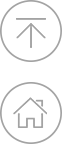团圆的愿望
“阿结,国庆节回来吗?” “妈,我可能回不了。” “哦,”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那,那你安心工作吧,过节自己加点菜。” “你们也是,好好保重自己。” 记不清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多少次。母亲总是在所有的节日来临之前,习惯性地给她“远嫁”的女儿打个电话,看看她能否回来。 说“远”,其实广州到深圳不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对于几乎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城市的母亲来说,这跨城的距离,就是见不着面,生病了也照顾不了。 从前母亲给我们讲她舅妈的故事,说女儿陆陆续续都嫁出去了,自己一个人坐在门槛边上哭。母亲一辈子也生养了五个孩子,除了弟弟未成家和我嫁得稍微远了一点外,其他三个女儿都把家安在了与娘家同一个城市里。平常女儿女婿登门,儿孙绕膝,母亲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也不顾自己的风湿腿疼,常常张罗着给孩子们包粽子、蒸甜糕。只是她每每念及我,就总觉得有遗憾,大姐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倒是母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难过之情。 这种隐忍,在中国式的亲子关系中是很常见的,父母和儿女,谁都不轻易向对方说出自己的难处。不过,那一次次细心的电话询问,就足以表达母亲期盼我回家团圆的渴望。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更因为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近几年我回家过节的次数屈指可数。母亲大多数时候是理解的,但偶尔也会抱怨一下“这么严格啊”。其实,不光是我要常常在节假日坚守岗位,作为警辅人员的大姐和身为护士的二姐、妹妹,也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假期。我以为母亲早已习惯这种“不圆满”,但她对我不能回家过节始终充满遗憾。 中国人喜欢把每一个节日变成举家团圆欢庆的日子。张灯结彩、烟火璀璨只不过是节日的点缀和注脚,团聚,才是过节真正的意义内核。于是,有了蔚为壮观的春运,有了长龙般的车流。万水千山,都只为了回家看一看。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我所就读的学校都是步行5至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每当我踩着上课铃声,从容地走进教室的时候,总会感叹“太近了”。于是,从上大学到选择工作地,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努力拓展着自己的生活半径,直到父母再也够不着了。 然而,随着离家的日子越来越久,我开始思念我的家乡、理解我的父母。离开成长之地,我以为只是扩大了自己与父母的同心圆,但在母亲心中,这距离更像是一个圆缺损了一角。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一家人的团圆,于是也成了节假日奔流在高速公路车海中的一员。每一个可以回家的节日,我和丈夫、孩子都会奔走在归途。在回家的前一天,向来睡眠质量极好的我,总会莫名其妙地失眠。丈夫取笑我,让我不要太紧张,只不过是回一趟家而已。 我想,回家已经成了漂泊异乡的成年人回到原点、寻找生命之根的一个仪式。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次在路上摔倒,一直哭喊着却不认得回家的路,直到天快黑了母亲循着路找来,把我领回了家,那种无助的感觉毕生难忘。 少年时叛逆挣脱,我曾经以为回家只是为了满足父母想团圆的愿望,中年后方才明白,一切的出发和远离,最终都绕不开家这个原点,回家团圆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渴望。 (作者单位: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出入境签证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