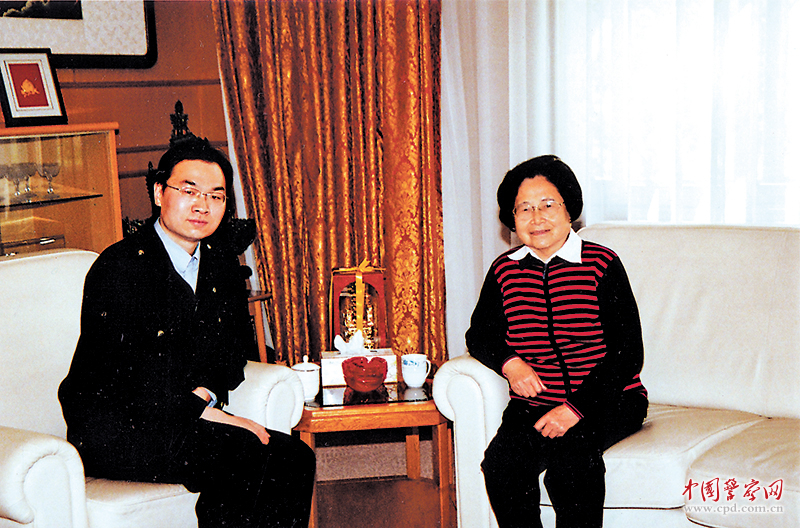
故居里的家风印记
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翁育峰
去年,我回到了翁氏故居。站在门槛前,轻抚着斑驳的青砖,耳畔是姚江水汩汩流淌的声响,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宅,曾是我高祖、曾祖们、爷爷们以及父亲兄弟姐妹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它承载了家族百年的沧桑变迁,更镌刻着一段段家风故事。
跨过门楣,一副柱联映入眼帘:“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看过那代代相传的“家训十八则”,我驻足在姑祖母翁郁文和姑祖父乔石委员长的介绍区域。一些历史就像一束光,穿透了岁月的尘埃。我的手指轻轻抚过展厅的玻璃,脑海里回想起姑祖母对我讲过的故事。
“立身以正,处世以诚,修身以俭,报国以忠”——家训墙边,姑祖母的照片还是18岁时的模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她只身一人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徒步百里投奔新四军。临行前,曾祖母含泪问她:“你舅舅在同盟会、在国民党都是中央要员,你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姑祖母只回答:“报国以忠,国难当头,忠字不在庙堂,而在民心。”
父亲曾说过,姑祖母从不提自己的功绩。即便晚年回乡,她也只说:“我是余姚的女儿,我这辈子最感恩的,是小时候老师教会我‘忠’字。”我突然明白:家训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选择。
抗战时期,姑祖母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鲁迅学院学习。她告诉我们:“我进鲁迅学院后,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真如久旱逢甘霖!我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能否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青年人有什么前途?’等等,全都迎刃而解!思想上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抗战胜利后,姑祖母先后在上海发动学生运动,担任党主办的《联合晚报》记者和《青年知识》杂志特约编辑。在那段岁月里,她以笔代枪,用文字传递党的革命思想,激励民众奋勇向前。
峥嵘岁月中,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紧相连,每个字都是家国同构的注解。为国尽忠时,家风是铠甲;为家尽孝时,国运是归途。
1993年,姑祖母带着乔石委员长的题字回到余姚,站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前,她用余姚方言说道:“我是喝姚江水长大的。”当她提笔在留言簿上习惯性地签下“郁文”二字后,又郑重补上“翁”字。这个细节,让老家人都动了情。姑祖母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一生隐去姓氏,却未曾忘记自己的根。
2012年,姑祖母在母校慈湖中学110周年校庆时与师生座谈。她说:“我出去许多年了,我这辈子都对母校怀有感恩之情,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姑祖母见面虽少,但她那“人如稻穗,越是充实饱满,越应谦逊低头”的家风教育,早已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离开翁氏故居时,夕阳为老宅铺上一层温暖的金色。那一刻我恍然领悟:“最美的家,从不是高墙华屋,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根系;最美的我,永远是家风涵养下,那粒努力成长的种子。”

人生底色是清正
办公厅 刘元元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民警。30多年的从警生涯里,他就像一棵扎根泥土深处的老树,枝叶伸向人间烟火,却始终保持人生的底色——清正。
“与老百姓打交道,没有什么高明的招数,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立得住,一身清正才对得起这身警服。”这是父亲常对我说的话。父亲所任职的乡镇派出所,人口密集、人员混杂。有人私下劝他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父亲却将腰板挺得更直。在那里工作的30多年间,父亲从未私下受过请托。他常说的两句话“讲原则的事,得罪人也不怕”“做人讲规矩,做事讲原则”,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次,父亲的一个朋友想办事,要把户口年龄改大,求他帮忙,他没有办。一个朋友在当地办厂,带着礼物上门,想请他帮忙站台撑腰,当场被父亲严词拒绝。但是对于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他从来都是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面。在摄像头、智能手机还没广泛应用的年代,有一次,父亲托我给他买一个卡片照相机,我问他打算做什么用,他说有群众反映菜市场里有几个惯偷,派出所接到过几次报警却总是拿不到切实的证据。后来,父亲揣着我买的照相机,连续在菜市场蹲守了一周,最终成功捕捉到惯偷行窃的画面,顺利将那个盗窃团伙绳之以法。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总是很忙,地处远郊的派出所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常常一离家就是一周。他走遍了辖区每一户人家,大家也都知道他是热心肠的“勇哥”,都说“有困难找勇哥,错不了”。在看守所工作期间,父亲不仅要承担值守、内勤等工作,还主动教育帮助罪错青年。这些事情从不曾听他提起,直到他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才从一堆表彰证书里发现了几封泛黄的信件,那是曾在县看守所关押过的年轻人寄来的。“您让我知道,人要活得堂堂正正……”字里行间都是对父亲教育引导他们改过自新、走上正确道路的感激之情。2016年,当我穿上警服走进公安部大楼时,父亲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和自豪,同时反复嘱咐我,做警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肩负一份使命、一份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得为群众办实事,更要讲规矩、守纪律、讲原则,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在看守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又回到了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工作,父亲落下了一身病痛。临近退休时,派出所所长提议帮他调动到清闲一些的岗位,或是申请提前退休,但父亲婉拒了所长的好意,强拖着病体坚持工作。派出所工作有时候深夜警情一个连着一个,常常是刚处理完这家的夫妻矛盾,又忙着去化解那家的兄弟争执,月光拉长他深夜出警的背影,沙哑的嗓音融进黎明的雾气里,往往回到所里已经是后半夜。2020年全国两会前夕,已经在办理退休手续的父亲得知局里安保任务繁重,毅然返回岗位,和同事们一起值守了最后一次安保勤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4年多了,每当我走过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菜市场依旧喧闹,却无人有失窃的担忧;当年他帮扶过的青年,已经可以自食其力。“家风正,则后代正”,父亲为我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就是一颗永不蒙尘的从警初心,这一切早已融入我的血脉。

纪念章里的时光记忆
督察审计局 刘芮含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老式木隔窗,在泛黄的墙面上投下斑驳光影。92岁的姥爷坐在藤椅上,胸前那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晨光的轻抚下流转着温润光泽。打开时光的闸,一段段饱含深情与力量的岁月往事就此缓缓展开。
1950年寒冬,朝鲜黄草岭的阵地硝烟弥漫。年仅17岁的姥爷作为炮兵装填手,正用已经冻裂、布满血口的双手,奋力将炮弹推进炮膛。直至今日,姥爷都清晰地记得,炮弹尾翼上凝结的冰碴,像极了老家屋檐下垂挂的冰凌。炮弹出膛的轰鸣,震落了掩体顶棚厚厚的积雪,而美军反击的炮弹已撕裂空气,带着死亡的威胁呼啸而至。“轰——”一声巨响,强大的气浪将姥爷掀翻在战壕里,飞溅起来的冻土混着弹片从头顶划过。姥爷在硝烟与尘土中挣扎起身,伸手摸到的是黏稠的混着冰碴的红色泥土,那是战友的鲜血。“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守住阵地,这是连长告诉我的!绝不能退!”保家卫国的誓言在血色中愈发清晰,如同黑暗中永不熄灭的火焰。
而在我的记忆里,每次去姥爷家,总能听到那首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家人团聚时,姥爷都会戴着他的老花镜,给孙辈们讲党史讲战场故事,总是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强调:“忠诚于党,干工作就不要想着发财,干工作也别想着当大官,而是去干大事,去干造福人类的事情。”
大学毕业时,我参军入伍,姥爷送我一块他亲手雕刻的梨木镇纸。正面“清正”二字刚劲有力;背面“慎独”字迹内敛却透着一股坚定。后来,我转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时,姥爷又送了我一份礼物,是一个补了12个补丁的旧军包,包面上用红线细密地绣着“忠诚担当”,我明白,这里面承载着一位革命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与谆谆教诲。
姥爷的手工活做得很好。小时候,看着姥爷熟练地摆弄各种工具,打造出一件件精美的物品,我笃定他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木匠。比如他送我的那套樱花粉色家具,从寻觅合适的木材到五金的搭配,再到切割、组装、打磨、上漆,每道工序都凝聚着他的心血,那是独属于我的、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可随着年岁渐长,我才明白,做手工并非姥爷的营生,而仅仅是他热爱生活、享受创造的一种方式,那些小发明小创造,是他对生活热忱的见证。
在姥爷的生活哲学里,“浪费”二字如同阵地上未引爆的哑弹,必须谨慎排除。搪瓷杯磕掉瓷就缠上电线继续用,收音机哑了嗓就换上自绕的铜线圈,就连孙辈玩坏的铁皮青蛙,经他巧手改造,竟成了精妙的削笔器。50年来,但凡家里有物件损坏,姥爷从不急着丢弃,总能在一番敲敲打打后让它“重生”。若是家里缺了什么物件,他就去找些边角料,叮叮当当左拼右凑,一件崭新实用的东西就诞生了。姥爷用他的勤劳与智慧,为我浇筑起抵御物欲横流的堤坝,那些经他手修复或诞生的物件,都在将姥爷勤俭持家的治家格言默默诠释着。
当然,姥爷并不只是对“旧东西”偏爱。去年除夕,我为姥爷姥姥添置了一套智能家居,原以为他们会对这些新玩意抗拒,没想到姥爷眼里满是好奇,拉着我让我教他如何使用智能马桶、智能窗帘以及智能照明系统。学习时,姥爷还念叨:“这智能家居有节电模式,可以使用绿电,咱们得跟上国家碳中和的步伐。”从一个90多岁的老人口中说出这些新词,令人惊讶,却也让我明白,关注时事,心系党和国家早已成为他的习惯和信念。姥爷常对我说:“人真正的老去,是思想不再更新。我现在虽然走不动了,但我不觉得自己老。当一个人思想停止更新,不再学习新知识,那才是真正开始变老!”他用行动诠释着自立自强,在岁月的磨砺中坚守着奋斗精神。
去年冬天,表弟用现代科技复原了姥爷当年的炮位三维模型。当虚拟影像中的年轻炮兵与轮椅上的老人隔着屏幕对视时,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姥爷那布满老年斑的右手,依然下意识地保持着紧握炮弹的弧度。那一刻,新旧时空的光影在交织流转,照见了不同时代的他,照见了相同的信念和精神。
姥爷的纪念章,就像一个时光宝盒,早将最珍贵的传家宝悄悄藏进时光的褶皱里,那是经历炮火淬炼、生死考验后传承的家风密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读懂父亲,是我毕生的功课
机关党委 张 丹
父亲出生于1947年。1966年高考前夕,风华正茂的父亲在志愿表第一志愿栏,郑重地写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在他踌躇满志即将奔赴考场之际,高考制度取消,“老三届”成为他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烙印。被历史的车轮裹挟着,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积极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去就是15年。受益于“老三届”的教育背景,父亲在当地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为农场学校的老师,后来还当了校长。在我8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返城,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他返城后的第一份工作还是老师——技工学校教导处主任。
父亲返回的城市是爷爷闯关东替他选择的第二故乡,那里背靠小兴安岭,距离黑龙江边只有半小时车程。当年,爷爷那一辈从山东一路迁徙而来,在仙鹤栖息的山冈卸下颠簸的风尘,在此安家立业、繁衍生息。虽然我只见过照片上的爷爷,但从父辈的口中得知,爷爷是个很有远见的人。在那个普遍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爷爷坚持把4个儿子都送去读书,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或许是因为心中有未圆的大学梦,或许是受教师职业的熏陶,又或许是受了爷爷的影响,父亲十分重视学习和教育。返城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自学考试,利用工余时间挑灯夜战,成为我们家第一位大学生。记得我初中毕业时,周围人都劝父亲:“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吗?读中专早点就业多好。”父亲有自己的坚持,他要求我必须读高中、考大学,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父亲不仅关心我的学业,还牵挂着家族里其他孩子的学习。他曾以爸爸、姨夫、三大爷、姥爷等身份,参加过我和3个表弟、1个外甥、1个外甥女以及我女儿的家长会。
1993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家里的座机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姨夫出车祸了。姨夫伤得很重,虽经多方抢救,最终还是瘫痪在床。那年,表弟才10岁。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姨夫,父亲心疼不已。他二话没说,将表弟接到我家,还承担起辅导他学习的重任。从小学到高中,在学校门口等待的、在灯下陪读解惑的、出席家长会的、甚至犯错时代替他爸教训他的,都是父亲。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表弟最终考取了省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边防军官。如今,又成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每每说起表弟,父亲总是既满足又充满慈爱:“这孩子,就是贪玩,不然还能更出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表弟对父亲的称谓也从姨夫改成了老爸,在姨夫缠绵病榻直至去世近30年中,我的父亲为表弟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
大伯母的妹妹一家从山东来投奔大伯母,在城郊以种地为生。那个时候,她们家生活拮据,便动了让两个儿子辍学打工贴补家用的念头。父亲听说后上门劝阻,还从自己不太富裕的工资中拿钱给两兄弟交学费。两兄弟读高中时,父亲把两兄弟转到离我家很近的学校,方便他辅导功课。那些年,两兄弟的家长会都是父亲参加的,这份关爱和温暖支持着两兄弟顺利读完高中并在高考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如今,看到他们有发展有出息,父亲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两兄弟也始终记得父亲对他们的情谊,在他们心中,父亲与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不是最近的,却是最值得他们敬重和感恩的。
随着城市煤炭资源的枯竭,不少煤矿工人都面临下岗的困境,两个表姐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家庭经济收入的下降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孩子学习方面的投入。这时,父亲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看着两个孙子辈的孩子面临失学的风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认为,在读书这件事上坚决不能掉队。他把两个孩子接到家里,我的母亲照料他们的生活,父亲帮忙补习功课。在我父母的悉心照顾和严格指导下,两个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后来也都考取了理想的学校。他们俩的成长让父亲的家庭教育事业再结硕果。
我在北京参加工作以后,父亲跟随我来到北京生活。大女儿上小学时,父亲再一次承担起了接送和辅导的职责。他不止一次顶着满头白发,给我的大女儿开家长会。大女儿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高兴得就像个孩子。如今,父亲即将步入“八零”后行列,却依然在我的小女儿的教育上殚精竭虑。他每天最乐于做的就是研究小学奥数题。他常自信满满地说:“辅导这个,绝对没问题!”
齐鲁的基因、东北的风土,赋予了父亲积极上进、诚实善良、耿直热心、重情重义的性格。身边亲友提起父亲,总是由衷地称赞他是个“好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却一直身体力行地教导我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见过父亲的人都说,我的相貌随他。形似因是血缘所致,神同实为教化之功。注重家教、乐于助人只是父亲众多好品质之一,他的精神家园以孔孟之道为根基,以更为广阔的爱为底色,延伸出许多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读懂他、学习他、成为他既是传承之要又是我辈之责,值得毕生去修习、去感悟、去践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父亲的引领下,我和我的同辈乃至后辈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的过程催人奋进、乐在其中,令人心生温暖、倍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