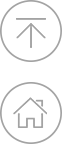骆一禾:与青春有关
2011年11月08日 03:0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中国青年报 · | 2011-11-08 03:02
 总得有20年了吧,年轮一岁一岁地长,我们的心一点一点灰下去。在零零散散的回忆中,零零散散的诗人被慢慢聚拢,经过组合的他就鲜活起来——年轻的他,年轻的他们与她们,正走在20多年以前北京的老街上。那条街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街,方圆多少里都是暗淡的北方灰。旁侧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拆旧翻新。 那是一个热爱诗歌的年代。那时候商品还没那么多,网络还没那么繁盛,美女还没被批量生产,人心还没那么涣散,青年人还爱着诗谈着理想。骆一禾刚刚从北大中文系79级毕业分到《十月》杂志主持“十月之诗”。他和海子、西川一直被称为“北大三才子”,但是他多愁善感、沉默寡言,常常被遮蔽在他们的光芒里,做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尽管他已经在《诗刊》、《上海文学》、《花城》、《山西文学》发表诗作几十首,留下2万行诗作及数万字的小说、文论。那时候的他,年轻,单纯,沉郁,谦卑,爱激动,书生气。 《骆一禾的诗》终于出版,他在《生日》中这样写:虽然我们也有不幸,我们最美好的,还在燃烧……人们可以永远地爱。祝男孩子们健康,他们是古怪的青铜,生来就是严峻和永恒。 他激情澎湃地描述《长征》:这是一条伟大的道路,首先写在亚洲中部,后来写在了世纪的内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心脏,把历史交给了农民。和历来的棉花不同,和历来的麦地不同……从人群上说,和军阀和绅士们,绝对不同! 他满心沉浸在年轻里。他说:星座闪闪发光,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只见心脏,只见青花。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书在北方写满旋风内外……太阳上升,太阳作巨大的搬运。最后来。绿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 可以想象,那时候热爱诗歌的他,他们和她们,曾经在旧世纪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背对着太阳走路,影子被抻成卡通片里不合比例的修长。他用脚踢地上一块一块的石子土粒。踢远了,走过去,像足球队员罚点球那样,姿势停留在某个造型上起脚再踢。然后漫不经心地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头发被风吹得四散。 1989年5月的一个诗会上,他激动地说着话,忽然倒在女友怀里。那天是黄昏时候开始起风的,地上的尘土、雪糕的包装、塑料袋和废报纸在角落里打着旋儿,空气中飞沙走石。他们的话也像是被土粒撞飞了,没有再连成整句子。后来她回想起来,他们的聚会本应该风和日丽,花好月园,然而却乌云翻滚、飞沙走石的,像50年代老电影的艺术手法。但那个时候的他们年轻得什么后果都来不及想,她只是慌忙穿过密集的人丛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但是不久,他的死亡报告就出来了,上写着“脑溢血,28岁”。那一个春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后来四季的风从哪个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一天的气息。 十年、二十年很快过去。朋友们还记得他小的时候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出版过长诗《世界的血》。但他的诗很少有单行本。他总是和海子合出诗集。他被诗歌界称为“在朦胧诗之后对诗歌进行了沉潜而深入的思考,并以思考为出发点,选择了一条修远之路。”但是终于,那些热衷于诗歌的朋友们,也因为诗歌的边缘而各自忙碌了。 新世纪的这些年,没有诗歌的都市,如一幅铅笔素描一样的定格:纷乱,仓皇,不安定。他们和她们,也已彻底忘记诗歌。他们为了人父为了人母。他们成了副处、正处、副局、正局。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正被裹胁进严酷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办公室弥漫着看不见的硝烟。他们受过骗也骗过人、受过伤也伤过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有钱,有房子,有网络,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心里是空的——这个世界,心里没有了诗,其实就什么也没有。而那些假装把句子断行的伪诗人们,正做着有奶便是娘的勾当,正在为生存利益失去基本的正义。堕落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但是他们还挺胸收腹地典见脸打着诗歌的旗号,真脏得让人恶心。 诗人骆一禾已经退场,他的名字正如诗歌的名字一样被遗忘。 |